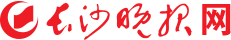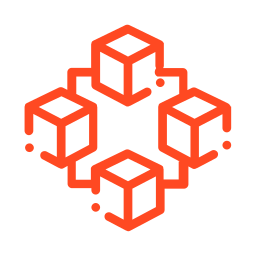老红牛
何静
父亲在公路局干了三十五年的养路工,名字里带个红字,工友们都戏称他为“老红牛”。他的臂力惊人,掌心布满厚实的茧子,被太阳晒成猪肝色的脸上总带着腼腆的笑。身上永远沾着泥巴和沥青,话少得像块石头。
父亲对待工作的态度,像极了他修补道路时的专注。无论酷暑寒冬,他总是早早抵达工地,用铁锹一铲一铲填补坑洼,将松动的石子夯得严严实实。单位领导常说:“‘老红牛’修的路,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。”他那把用了二十年的铁锹,木柄开裂又被铁丝缠了三层,却从不舍得换新——“能用就别浪费”,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我八岁那年,家里建新房子,老妈想要老爸在单位弄点材料回来,三番五次在老爸面前念叨,别人家某某某,都拿了几袋水泥了,公家的东西拿一点有什么关系呢?这时的父亲脸绷成了铁板,嘴唇抿成锋利的直线,露出两簇灼人的目光,说:“公家的东西,一分一毫我都不会要。”父亲在是非对错面前的这种坚持,成了我心中最坚实的道德标杆。
冰天雪地的清晨,父亲的咳嗽声像把生锈的锯子,一下割开寂静。我在被窝里迷迷糊糊听见了关门声,等我天亮起床,推开房门就看见那双结满冰碴的胶鞋。鞋面冻得硬邦邦地立在水盆里,融化的雪水混着沥青、泥浆,黑得像打翻的墨汁,母亲红着眼眶在清洗鞋子。只要下大雪,父亲就要早起,一是趁路面没人的时候撒上防滑料和融雪剂,二是要铲除积雪和清理路面。父亲的眉毛、帽檐结满了白霜,橘色工装冻得硬挺,活像挂了层冰壳的柿子,他搓着发紫的手指,瞥见我盯着他滴水的衣角,突然咧嘴笑了,冻裂的嘴角扯出细小血痕。他故意拖长调子:“哟,小懒虫醒啦?今天不要上学,等会下楼跟我一起去铲雪吧!”看着他后颈被雪水浸湿的头发一缕缕黏在皮肤上,细密的汗珠顺着发缝滚进衣领,我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有一年夏天,连日的暴雨冲垮了许多村落路基,交通中断,几十处塌方。临近退休的父亲在泥水里泡了整整一天。晚上回来,膝盖肿得像馒头,走路一瘸一拐。咳嗽声此起彼伏,起初是压抑的闷咳,胸腔仿佛有团化不开的沥青在翻涌。紧接着是剧烈的咳呛,震得风扇叶都跟着发颤,他不得不佝偻着腰,粗糙的手掌死死抵住胸口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我要带他去医院,他却摆摆手:“老毛病了,歇两天就好。”第二天清晨,我发现他又偷偷扛着铁锹出门了。
生活中的父亲是个脾气温和的“老好人”,小时候我和姐姐调皮捣蛋,打翻油瓶、扯坏窗帘,他总是笑着收拾残局,说:“孩子嘛,摔摔打打才长大。”家里来亲戚,孩子们把客厅闹得一团糟,他也只是默默整理,还笑着给哭闹的小孩递糖果。他的好脾气,像冬日里的炉火,温暖着每一个家人。即便工作再累,回家路上总要绕去小店,变魔术般掏出我和姐姐爱吃的零食,西瓜泡泡糖的甜、果冻的滑嫩,填满了整个童年。
手心磨出血泡,血泡破成血水再结痂成茧,粗糙的手掌一如铺就的公路,变得越来越坚实。父亲这辈子没说过什么大道理,从来都是低头做事,就知道修路要修得踏实。他常说:“路修好了,人心就安了。”看着他日渐佝偻的背影,我忽然明白,父亲就像他修的路,稳稳当当,承载着所有人的信任。
如今他退休在家,我也踏上了工作岗位。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在面对工作与生活时,也学着像他一样温和处事,耐心和人沟通。在我眼中,父亲将对工作的坚守、为人的清正与家庭的温情,化作涓涓细流浸润着我们的生活。
>>我要举报